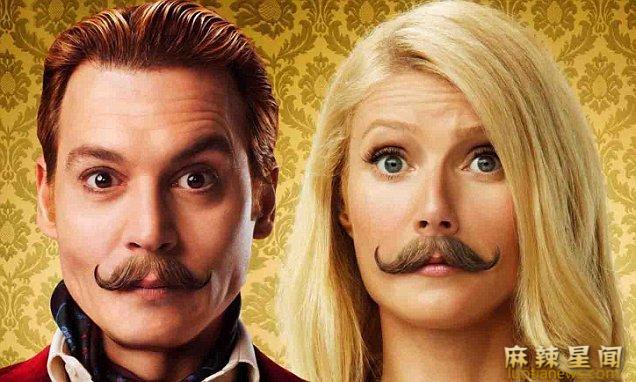今天为大家带来寻找故乡

我在出生地待了十八个年头,在上大学的城市混了四年,在第一工作地度过了两年多,在第二工作地、也就是现在的居住地梦幻般地生活了三十五个年头。老于世故的生活智者会说,你的出生地是你第一故乡,上学和工作的地方是你第二故乡。这种说法听起来无懈可击,只是对于我长时间工作生活且将终老的现住地来说,略显不公。我一方面承认生活的智者为我人生各阶段的归属所做的划分和确认,另一方面,又在内心进行坚决地否认。因为我一直还在寻找故乡,因为我没有故乡。
我的否认,我的寻找,我的飘飘无依……全都缘于我对故乡这一概念与众不同的认知。对我来说,出生、工作、学习和故乡没有必然关联,甚至都不重要。亲近和紧密所构成的人道现状总和更多的只是感情要素,启示的形象须让位于自由开放的没有神的神圣氛围。这种氛围可以一成不变,因为有了四季轮回、昼夜交替就足够了。故乡乃灵魂之所宅窟,是一个身心绝对自由而无负载的领域,它不仅仅是为了安放身心,而是为了让身心栖息、生长、舒展、繁衍,为了它的生生不息。在我看来,故乡须有最好的清晨,最好的午后,最好的黄昏和最好的夜色。那里的花草虫鱼、走兽飞禽、干湿阴晴,悉皆无害。那里不能有其他人,哪怕是最亲近、最可信的人,因为任何人的靠近都会形成压力。那里的房间墙壁上不可以张挂人像,通道和厅堂里不可置放雕像,因为在如此不动声色、毫无倦意的默视中,会产生身处监视器探头之下的不安和惶惑。那里也不可以有神,神的瞩目能将人变成囚犯,他总是披着黑色斗篷立于你心灵的归宿和遁逝之途。何况我是个容易产生某种或兴奋或忧伤情绪的人,在情绪激荡的中心,我会匆匆写几句,写在纸片或是墙壁上,此时我是绝对不能被干扰的。而在情绪相对平稳期,我则会写一些较长篇幅的东西,一些被逻辑推动、有条有理的东西。我会写《钓鱼法则》《狩猎罚则》《雷电规则》。但我不会抄经,我厌烦抄经却偏偏会背诵不少经文。我猜我上辈子该是和尚,饱受各种戒律束缚之苦,今再度为人便天生仇视规则,并带着报复心理去破坏规则。
然而,像我这样理解和定义故乡是不正常的,因为太人道了;是病态的,因为太健康了;是不理性的,因为太现实了。这就相当于一个有洁癖的人,就因为太干净,所以是病态。我对故乡的寻找所体现的正是我社交精神的洁癖。我一直试图找出我的这一洁癖的病因。事实证明我的寻找是卓有成效的,寻找到的证据证明病因并非前世为僧,恰恰是现世为人。
人与人相比,可能我比你心狠一点,你比我胆大一点;我比你笨拙一点,你比我滑头一点;我比你狂放一点,你比我谦卑一点……这些差别随着人的涉世成长,会渐渐被抹平或隐没,也会逐渐被拉开或加剧。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温和友善、平等自由的社会,则性格的差异会逐渐缩小,或者说性格的差别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会趋弱和淡化。反之,如果人们生活在一个缺乏友善,不公平、不温和的违反天道的的环境里,则差异将被加剧。
余华的《我胆小如鼠》让我记起我的小学时光,记起黄泥课桌、木板凳子和军人出生、腰悬一串钥匙的校长,当然还有鹅、狗和老虎。我不怕鹅,故而算不得胆小如鼠;我怕狗,因此胆子确也不够大。但我不怕老虎,因为我从没见过老虎,加上本人属虎,再加上听过武松打虎的事,心中不光不怕虎,甚至有点蔑视,也因此很不喜欢自己的属相。这种想法固然可笑,但你得承认垂髫之人有此想法的合理性。现在已经记不起儿童时代的我到底有多少可笑却该被认作合理的想法。我只知道那些想法让人羞愧、害怕,嚼碎后咽下肚子,和被消化过的食物一起排泄到了露天茅坑。
我从我们那些妙笔生花的作家那里得知,中国少年的梦想是彩色的,他们的童年生活是天真烂漫充满欢乐的。由此得知,和其他人五彩斑斓的少年时代相比,我的少年时代的天空总是乌云密布。暴雨和惊雷一直使我处于高度警觉、不安和恐惧的中心。
我试着分析造成我与众不同的成因,我觉得一果多因是可能的。比方说,来自天然的我的个性,比方说某种外因或多重外因通过我这种个性发生作用。单一病因的社会病例是鲜见的,因而我有理由确定我的主要病因是学校强加给我的那些各色学习榜样。他们高大光辉的形象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天赋让我觉得无法企及。那些榜样无一例外地给了我毁灭性的打击。
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间,学校为我树立了一个个人生楷模和学习典范。无论他们是热爱学习并卓有成效的典范,还是破坏学习志做新人的榜样,都从没给我带来好运。对于那些善于学习的典范,他们越说自己的成绩出自勤奋,我就越觉得他们是天才。一个不是天才的人怎么可能如此聪明,如此善于学习、热爱学习,并最终取得如此成就?有时我想,如果他们索性承认自己是天才,或者学校认定他们是天才,我可能还有努力一番,勤奋一些,争取把普通人的才智发挥出来的冲动。正因为他们不是天才,更让我望峰息心,自甘堕落。至于那些破坏学习的榜样们,尽管我内心很想仿效他们,而且仿效起来应该是不需动脑子的,可我偏偏又动起脑子。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他们毅然放弃学习的雄心,底气和本钱。而且我暗暗觉得真的什么都不学,只闹革命,终非正道,终究不是个事。但那个“不是个事”的事到底是什么,以我当时的脑子是想不出来的。事实上到了现今我的脑子已经不怎么好使的年岁,我也没想出那个不是个事的事是什么事。典范或者叫榜样或者叫楷模,据说他们会给人以走向人生高远目标的动力。但给我的却从来只是压力而非动力,破坏而非塑造,欺凌而非抚慰,并让我自贱自弃。
事实上,那些楷模,典范,榜样们,到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都没弄清楚。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个有着比槽钢还粗硬的名字的人竟然是个小女孩。相反,有着一个甜美如婴孩名字的人却是个年近五十的伧父。那时我们看不到照片,更别说视频。而我们看到的照片往往是榜样已不再是榜样的多年之后的类似漫画的图像。他或者她在一块被撕成碎片的泛黄发脆的报纸或杂志上,被我们发现。我们会仔细辨认图像下面的说明文字,我们往往会被他们眉宇间的英气折服。觉得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再被重视或是正在被批判,他们也是不同寻常的。因为能引起整个社会批判的人注定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有时我会在心里暗暗妒忌他们。对我来说,二十岁之前唯一觉得有些优越感的就是在填写那些莫名其妙的表格(可能是要被放进王校长口中的档案)时,我填写的是三代贫农。我的身边三代贫农的同学并不太多,他们的成分总有点瑕疵。和我沾亲带故、关系亲近的刘姓同学力气比我大,家境比我好,但他是中农,仅此一项,他就低我一等。我猜这是他应该妒忌我的地方。
等到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刚刚读完两年初中,进入两年高中阶段。此时我们的榜样又都由不学ABC,照样开机器的纯正中国人换成了各地各年的高考状元,特别是那些少年大学生,让你无法不惊为天人。那些天纵之才的神童不光是数理化学科的尖子,同时也是文科的奇才。他们写出的旧体诗词,在那时的我的眼里简直比李杜苏辛还有气势。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只记得有位少年天才一首词的最后三个字:乾坤赤。应该是“满江红”的最后一句。之所以记得这三个字,是因为我曾为此请教过我村里唯一上过私塾,读过三字经和增广贤文的秀才蔡公。蔡公身长八尺三寸,隆准深目,满脸荞麦状的麻子,长得像视频里的德国鬼子少校。当时我只觉得这三个字高妙,有力度,根本没去想乾坤一派通红有多吓人。蔡公解释说,乾坤赤,指的是革命红旗插遍全球,迎风招展,火海汪洋的意思。我说,五湖四海,红旗招展,是不是意味着都是被鲜血染红的?蔡公摸了摸稀疏杂乱的唇髭,严肃地说,这是伟大革命应有之义。
关于我们的榜样、楷模,我们的老师其实不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们多半是农村里曾经上过中学的人,被招募到学校做民办教师。他们举手投足和眉宇间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直率有余,是否憨厚则难以评估。王校长是部队转业的,属于公办教师,他夏天总爱穿一件丝绸短袖上衣,下身穿一条宽大的涤卡军裤,腰间系着从部队带回来的那条武装带,带扣右边挂着一大串钥匙,走起路来叮当乱响。他喜欢瞪着那对牛蛋一样的大眼睛恶狠狠对我们说,你们要能学到人家身上的一点皮毛,我就把我的姓倒过来写。他说的“人家”指的是那些典范,榜样。他每次说把他的姓倒过来写,我就情不自禁在手心里摹画倒着写的王字是个什么样。他几乎每次开会都会语气不善地大声说,你们谁要是上劳动课时开小差,或是把一只山芋藏在裤子口袋里带回家,老子就在你的档案里涂上一笔,保管你背一辈子黑锅。而我则觉得他在学生们身上扫来扫去的目光最终总有意无意停在我的脸上。至于他口中的档案,则像一块沉重还会爆炸的石头,一直梗在我心里——它总让我想到坐牢。作为小学生,我偷过山芋,偷过尚未脱毛的桃子,还有半生不熟的西瓜。我觉得他是知道我偷东西的事的,否则他的目光不会总落在我的脸上。这个人教了我七年的德育课,因为他是我五年小学的校长和两年初中的校长。在我大学四年的前半程,他一直是我的噩梦里现身次数最多的那个人。
我必须承认,很多年里,那些穿白衬衣的,穿工装裤的,穿裙子的,戴红领巾的,带袖章的,戴领章的,戴眼镜的,戴脚镣手铐的各色典范和榜样们没帮我什么忙,相反他们的高大形象和伟大业绩摧毁了我仅有的一点自信——一个山村农民儿子从贫穷和饥饿中保全的一粒米那么大的自信。他们无一例外成为我学习、生活中的梦魇,成为我成长路上的荆棘和绊脚石。他们本来是被好心请来帮助我的,但他们被包装成了天神,浑身长刺,衣裳带电,使我一开始就凭生分别心,意识到我和他们不属一个阶层,甚至不属一个世界,他们生活在到处是阳光雨露的芬芳世界,我甚至怀疑他们不吃五谷杂粮。他们被派到我的身边,热情而无私地拥抱我,把我贴身紧紧抱住,但他们忘了我需要呼吸。在高考结束差不多一个月后的某个雨天的下午,家住三里地外的同学忽然冒雨跑来跟我说,有人看到你的高考分数了,中学文科最高分。我说不可能的,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我嘴上这样说,却带着他走到屋后的菜园把一只我观察多日、确定已熟的香瓜摘下来,二人分吃。然后我对他说,我们去学校看看怎么样?他说可以,但不一定能看到,因为是数学老师的儿子翻窗进去偷看的。从我家到中学有五里地,我们打着伞赤脚往那里走,一路上我都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肯定没那么高的分,他们看错了。我知道,我的这句话是世界上最混账的言不由衷的话。我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我太想同学说的是真的了,是因为我太缺乏自信了。记得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只敢填写师范之类的学校,尽管那年我们是在已知分数的情况下填写志愿,我仍只敢填写最普通的学校。后来还是一位留小胡子、满脸青春痘的年轻教师看不下去了,他用几乎半是嘲讽半是强迫的的语调让我填写了我后来上的那所大学。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年我的分数是可以上南京大学的。现在我和我中学时一位校友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他曾经是我的中学的非典型性榜样。所谓非典型是指他仅仅是我们学校自己培养出来、只被我们学校认可的学习标兵和尖子。那时我总在一进学校大门的地方看到他的名字写在右侧的黑板上,内容是参加县里数学、物理或是化学竞赛获得的好名次。现在某大学做革命史教授的他依然多姿多彩,生龙活虎,生活得写意而放纵。和中学时代比,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再视其为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应该包括高压和摧折的力量。用榜样和典范来激励鼓舞斗志的办法大抵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至少对我是无效的,不但无效,而且起的是百分百副作用。人的才智和创造力也不都是在压力之下才能迸发出来。恰恰相反,最伟大的创造差不多都是在绝对自由的环境里完成的。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学、中学是否还像当初给我强树榜样那样为孩子们树立学习楷模。我猜路数应该无大变化,可能唯一不同的是不再树像张铁生、张玉勤那样破坏学习的榜样。但总有新内核的榜样诞生,总有像我这样身心孱弱的学生被榜样压垮。
那些榜样如附骨之蛆,吸附在我的精神上,蚕食他,使他饱受噬咬之痛,使其贫瘠荒凉。然而这些榜样并无恶意,我和他们不相识,更谈不上仇怨,他们从也不曾想到要来害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使我们在波谲云诡、人海茫茫的社会里对接,使我成为他们压迫、消遣、戕害的对象。
能够走出灵魂被压制,被管束,被摧残的、胆怯的过去,并非我获得了自我解放的能力,我不过是一个囚犯,意外获得地震的无心之助,它摧毁了监狱厚重坚实的高墙。然而后遗症还是留下了:从此我不再相信权威,也不再尊敬伟人,并对政治家抱有无法逆转的成见。真的就像许倬云先生所说,对伟大人物不再有敬意和幻想。那些被标榜成伟大善人或渺小恶人的人,无一不像我少年时代的那些榜样,被包装得不神、不圣、不人、不鬼。他们的身上添附了太多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使他们成为一种有害而重叠的幻象。至于政治家,其实并不适合用善恶好坏来评价,评价他们的标准只能是功过。因为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有邪恶的一面,都有非正义的属性。所以我对从政者向来只同情、不敬重,只理解、不参合。我一直怀疑我这样的评价方式和标准是否正确,因为我的灵魂是受过创伤的,我胆小如鼠,我的灵魂矜持、谨慎,怯懦、自卑,多疑、伤感,一生都战栗于被害妄想的惶然之中。走出监狱的我,徘徊歧路,侧身天地,找不到故乡,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人们应该理解我对故乡的定义不是不切实际,而是太切实际,也当理解我寻找故乡的千难万险和种种苦楚,如同所有宅心仁厚的贤良方正经常乐于表现的那样,也为我掬一把同情之泪。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寻找故乡

 小尔木基
小尔木基